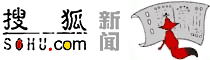|
主笔:舒可文
导读:长征,记忆中故事
《长征——一个行走中的视觉展示》,记忆中的记忆
计划
随着《长征》展览计划的不断扩大,从4年前卢杰的一个梦想到今年初开始具体组织,到目前为止被纳入到这个计划中的展览已经有20个之多,参加人数已经逐渐增加到112人,除了国内艺术家,还有已经在美国工作的蔡国强、徐冰等,以及像美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发起人朱迪·芝加哥等西方艺术家加入。
7月1日,主要组织者连同一部分艺术家和一个摄影记录队伍就要上路,大部分参与人将在路途中陆续加入,当然他们都是坐飞机去。他们将以当年红军长征的起点——江西瑞金为开始,沿长征路线选择20个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做展览,放映与相应地点有意义关联的电影、记录片,例如安东尼奥尼的《中国》,预先设计的一些讨论题目也随之展开。每个地点停留7天。预计在3个月后到达陕北。
这是一个行走中的大型展示系列,也是一系列当代艺术和视觉文化讨论。在长征路上的活动完成后,所有在这个过程中创作的作品和形成的文本、影像将作为整个活动的下半部分,在国内外七个艺术馆巡回展出。
卢杰是此次活动的发起人,他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做过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做过画廊,1998年去伦敦读美术展览策划专业,在此期间开始想象这样一个计划。由于规模过大,也只是一个想象,但他无法回避。因为对他来说,在童年和少年以至后来所经历的社会主义生活经验、文化经验不但已经积淀为人们最深刻的记忆,也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形态。这些经验渗透在当代中国视觉文化的各个角落,成了当代中国艺术时隐时显的最重要资源。而我们熟知的中国当代艺术却在成熟的展览制度中,难有更大空间来使用这些资源,在这种制度中的大部分作品注重意义,而不是经验,说教甚多,观念太强。所以对他来说,重读革命史,整理社会主义记忆和生活经验便成了不容回避的冲动。
为了让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他到纽约注册了一个基金会,专门为此征集资金。但几年过去,他几乎一无所获。今年他等不及了,带着120万元的自家钱开始筹备。对这么一个跨越了20个地点的庞大系列展览,这点资金根本难以支撑。好在上路之前,组委会在北京藏酷艺术中心做的一系列阐释、讲座等活动,得到了有意参加这个计划的艺术家们的谅解,很多在惯例中应该由组织者提供的资金支持顺利地由双方分担。
踩点
过去4年里,卢杰4次去长征路,今年初他和艺术家邱志杰又做了一次详细考察。之所以选择长征路线,是因为长征故事所具有的事件戏剧性和场所的丰富性,所涉及的课题复杂性和根本性,都给他们提供了重构的极佳线索。
长征路上的踩点记录了很多与主流展览无关,却更让他们兴奋的艺术家们的创作。在江西某地有一个公安局长傅新民,几十年来不懈地做根雕,从传统根雕方法开始,逐步发展成抽象和意象性的根雕,用千姿百态的根造型创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平行的抽象造型世界,又以此为基点反过来涉及现实世界。对他们具有启示意义的是,傅新民完全超越了职业艺术家与业余艺术家的界限。
在延安他们遇到了一个以做毛泽东塑像在当地闻名的艺人王文海。他原来是延安纪念馆的讲解员,70年代时西安美术学院教师来此地搞创作,王文海为他们当模特,美院教师在创作同时办了一个民间泥塑学习班,王文海是学习班学员,从此开始做毛泽东的泥塑像。30年来,他已经创作大小各种神情的毛主席像一千多个,这些作品也偶有出售。
在云南他们被引导到一位名叫罗旭的奇人的城堡,这是一个形态异状的处所,它由一组像小山包一样的土堡组成,罗旭自己设计,自己建造,严格地说它并不是设计的结果。因为他完全不懂建筑,只是心中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形象要完成,所以所谓的图纸只是个外貌。在施工中,搭起来的“建筑”一遍遍地倒塌,一次倒塌就是一次试错,在不断试错中他完成了这个异想,那里面现在就是他自己的雕塑陈列馆。那些在远离美术馆制度的视线下的雕塑一被发现,马上被评价为极具当代感。
从这些考察中,他们看到的是这些不会被称为艺术家的创作者们对自己经验的忠实,没有美术馆的关照,却依然保存着完整的创作激情。所以他们相信,该活动“决不是发起者一时的心血来潮或一己的癖好,它所面对的是我们这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梦想和情结,共同的创伤和焦虑”。整理工作既不是把这种经验和记忆当作社会生活中的保守因素进行消解,也不是以怀旧心态去神化历史。在他们看来,《长征》系列活动也将是一个隐喻,绝不是一个观念性展览,而是提供一种扎根于民间色彩和地方生态的艺术创作和展示的模式。
7月1日,计划在江西叶坪革命旧址展出公安局长傅新民的根雕和北京雕塑研究院展望的不锈钢假山石。在代表两种乌托邦意义的材质和演绎中,也许能够检索一下我们精神深处的乌托邦观念。在这里新媒体艺术系列展映,新媒体包括实验摄影、实验录像和电影、互动多媒体和网络艺术种种形式,是80年代以来风行的艺术形态。它对技术乌托邦有正反两种态度,既要与技术进步保持持续的对话,把自己看成未来的艺术形式,通过更新和变革媒介来催动思想变革的普通信念,又要对技术进行清醒的蔑视。
到遵义的时候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和参加活动的中外艺术家来开研讨会,在远离中心、地处内陆的小城遵义,能让大家来交流各自的中国经验,探讨彼此的现实局限和真正有利的资源,讨论艺术实践中的本土语境的重要性。两位组织者说,之所以选择遵义说这个话题,“正是要利用这里独特的历史语境,当年在这里,一批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本土语境相结合的共产党人,结束了生硬搬用共产国际教条的知识分子在红军中的统治,这对今天当代中国艺术的实践有何意义?”
类似的设计有很多,这些设计可能还会有理论上的收益,但是在伴随的艺术展览中,却有不少仍然是在各种常规展览中形成了的习惯方式,因循着一贯思路。比如使用旧衣服做材料的,只是改变为在长征途中收集旧衣服。卢杰在提交的方案中看出,很多艺术家还是习惯于风行了10年的反讽、调侃方式。长征以及它遭遇的困难和问题的解决都是在行走中完成的,也许,策划人在做计划时想到的问题也会在行走中不断更新,习惯于美术馆制度的艺术家也许会在行走中激发出更主动的激情。
3个月以后见。
根据地
徐冰一接到这个计划邀请,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现在他还没有确定下来方案,但是他到延安肯定想找革命题材的著名画家刘文西,刘文西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线索里成功的艺术家。而徐冰说他自己在西方这么多年一直忘不了这个讲话,他的很多作品也透露着那里面告诉他的东西。比如,艺术为人民。
1999年徐冰参加芬兰国家现代美术馆组织的“喜马拉雅山”计划,该计划邀请6位艺术家到尼泊尔登山旅行,一个月以后每个人提供一件与登山有关的作品在美术馆联展。他说,“这不就是我们以前的‘深入生活’吗?”一到尼泊尔,看到飞机场就像我们的小县城的长途汽车站,下意识地拿出相机想作记录,但是不知道该拍什么该对什么感兴趣,那种穷很难让人还想着现代艺术。就觉得好像是很多年前西方人看中国的眼睛在看这个地方,那我等于在用别人的眼睛看东西。因为有这个背景,我就不太容易那么潇洒地做艺术。最后我是用文字组成了一幅写生,是树的地方写上树,是山的地方写上山,像画,也像日记。回芬兰的时候还做了一个捐款箱,展厅墙上是美术馆与尼泊尔方面商讨捐款如何使用的通信,是向捐款人的说明。后来这笔钱用在尼泊尔一个山区小学的建设上了。美术馆的人评价这个作品——如果它是作品——说,“它表现了徐冰的社会主义文化背景”。
徐冰以他的新英文书法写的“毛主席说:艺术为人民”的旗帜,挂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大门前时,是他第一次明确使用自己的中国经验,也是想正视自己的这种教育背景。他说:“因为我们说话、思维的方式,看事情的态度都与那时候的教育关联着。到西方工作后,又看了一些毛选,感觉不一样了,比较明确地用这些思想做武器了。尤其是针对西方艺术传统,我只有这个武器,没有什么可选择的,只有如何使用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能看到,很多中国艺术家都在有意无意地使用,虽然方法不同,因为这是回避不了的。”这种背景也体现在他做的一些更大胆的作品上,比如两头文化猪的交配。他自我反省说,当时的展览评价说中国艺术家走得很远,“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没规矩,严格地说,我们根本没有完整的知识训练,所以也就不受知识的制约。总想对现有艺术做方法论上的改造,所谓当代的艺术也是一种文化革命,当然不是指具体的事情。”
说到《长征》展览计划,他说,虽然具体的方案有点形式主义,但不能不承认,“它挺特殊的,至少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和这个计划有一种知识上的特殊关系。另一个意思是,也算是给中国当代艺术寻找根据地”。
|